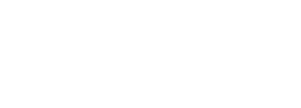日前,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孫強團隊經過5年的不懈努力,突破了體細胞克隆猴的世界難題,首次順利培育出體細胞克隆猴“中中”和“華華”。該項成果于1月25日作為封面文章在線公開發表在生物學頂尖學術期刊《細胞》上。 在此之前,盡管羊、豬、牛、馬、狗等哺乳動物的體細胞克隆都陸續順利,但與人類相似的非人靈長類動物(獼猴)的體細胞克隆卻仍然是生命科學領域沒解決問題的難題。 為何“名不見經傳”的孫強團隊能搶先一步獲得成功?他們的順利有哪些救贖?記者近距離認識了這支中國團隊。
面臨根本性科學難題堅決不退出,是順利關鍵 “針對根本性的科學難題,堅持不懈地把它攻下,是這個項目順利的主要原因。” 在談到孫強團隊順利原因時,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意中心主任蒲慕明院士說道。 時間推倒返回2000年。 那一年,在經過6年的嘗試告終之后,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杰瑞·沙騰得出結論“基于‘多莉’(克隆羊)的克隆技術構建克隆猴是權宜之計的”結論。
旋即,“克隆猴”研究在美國生命科學界遇冷。 盡管判處了“判處死刑”,但因為“克隆猴”對人類的重要性,全世界仍有不少科研人員為攻下這個難題繼續做著希望。 2007年,昆明理工大學靈長類轉化成醫學研究院院長季維智和中科院動物所周琪團隊的研究找到,“體細胞克隆猴的胚胎是可以超過囊胚階段的”,這就將此前沙騰教授指出“胚胎發育打破沒法八細胞期”的觀點駁斥丟棄了。隨后的2010年,美國的米塔利波夫團隊順利重制了克隆猴胚胎,并將胚胎發育的時間縮短至81天。
雖然,這枚胚胎沒有能最后圈養,卻讓大洋彼岸的蒲慕明看見了期望。 2012年,在浙江烏鎮舉辦的中科院神經所非人靈長類研究小型專題研討會上,蒲慕明明確提出神經所一定要立刻積極開展猴體細胞克隆的工作,并把這個任務轉交了孫強團隊。
他對孫強說道:“猴子分娩周期是160天左右,美國科學家還差一半就順利了,我們也很有期望——只要作好只剩的一半。” 于是,在沒現成平臺和猴子基地的情況下,孫強帶領以博士后劉真居多的團隊打開了這項研究。
孫強說道:“我們當時在蘇州西山出租了一塊地方作為研究平臺。那里環境較為破舊,我們17個人要輪流買菜、吃飯。一周7天,每天24小時交錯當值,日夜照料1000多只猴子。
” 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孫強團隊仍然沒退出,總算解決重重困難最后攻下了這一世界難題。 劉真說道:“這期間,告終有很多次,但是團隊每個成員仍然沒退出期望。我們指出經歷一次告終就是回避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告終后更多的是調整心態,分析告終原因,找尋解決問題途徑。” “猴子是靈長類動物,成本很高,不像其它實驗可以大大去嘗試。很多實驗室可能會因為告終次數多停掉實驗。
”蒲慕明說道,“我們一開始也沒做到能突破,也是在冒險。但一旦我們趁此這是一個十分最重要的問題,就一定要堅決把它制成。” 把有數的技術展開構建和優化,也是創意 據媒體報道,曾參予克隆全球首只體細胞克隆動物“多莉”羊的英國科學家威廉·里奇在一份聲明中說道,克隆“中中”和“華華”的方法與他們克隆“多莉”的方法“相近”,但有了一些技術細節的“改版”。 蒲慕明也坦白,孫強團隊沒發明者什么新的技術,而是把當前世界范圍內所有關于“體細胞克隆”涉及的近期技術展開了構建和優化。
“是把有數的技術精妙地用于,獲得了結果。” 蒲慕明舉例說道,比如之前米塔利波夫的實驗之所以沒順利,原因之一有可能是在核移植這一環節中做到得還過于精細,“我們就在這項技術上做到了更進一步的優化。” 孫強團隊的順利,高超嫻熟的顯微鏡操作者技術功不可沒。
猴的卵母細胞容易辨識,“去核”(核移植的步驟之一)可玩性大,對技術的拒絕極高。如何才能明晰較慢地辨識出有細胞核?團隊科研人員研究找到,只有在偏振光太陽光下,細胞核才能在顯微鏡下顯露出“身影”,于是就要求在去除細胞核時利用偏振光設備來構建細胞核的精確定位。 為了盡量減少細胞受損,減少胚胎存活率,整個操作者時間必需越高就越好。
劉感嘆“去核”的主要操作者。為了能在“去核”過程中做較慢精確,他練就技術幾年,最后能超過平均值10秒放入一個核。 劉真說道:“整個核移植操作者的基礎我是利用小鼠卵母細胞展開鍛煉,差不多倒數三四個月每天鍛煉8—10個小時。
小鼠的基礎嫻熟了,從鼠到猴基礎操作者并不需要相當大的沖刺,只是猴卵母細胞‘去核’更加無以,必須一個新的適應環境和嫻熟的過程。” 利用顯微鏡設備,劉真用一雙巧手重復鍛煉,在最短時間內、用大于損耗已完成“卵母細胞去核”和“體細胞重制”工作,為先前的克隆工作奠下最重要基礎。 除了操作者技術,孫強團隊另一個順利的關鍵是尋找了體細胞去甲基化、乙酰化的適合配方。
“這也就是指此前華裔科學家、美國哈佛醫學院教授張毅等科學家的研究中受到的靈感。”孫強說道。 蒲慕明說道:“生物學很多沒突破的根本性問題,并不是說道必須研發新技術才能突破。
創意不一定是建構新技術和新的理論,把有數技術展開構建和優化,這也是創意。”更加最重要的是,無法只做到漸進式、增量式的創意,必需針對領域中普遍認為的難題、有里程碑意義的目標展開大膽跳躍式研制成功,這樣才能在該領域獲得排在地位。 要想要獲得更加多根本性原創突破,需推崇本土青年創意人才培養 孫強和劉真二人都沒任何海外求學經歷,是名符其實的“土博士”。
去國外好的實驗室做到博士后,公開發表好的文章,再行回國正式成立自己的課題組是目前最少見也是比較更容易順利的一種模式。很多青年科研人員都自由選擇了這條路,但劉真沒。
2010年,劉真畢業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在他碩士二年級時,之后重新加入導師孫強的研究團隊,追隨他們一起攻堅體細胞克隆猴這一世界級難題。2016年,劉真博士畢業時,以他博士期間的學術成績,申請人到國外頂級實驗室是沒問題的。但劉真最后還是要求之后留下挑戰“克隆猴”的難題。
對于這個要求,劉真仍然沒愧疚過,“我實在國內當前的科研條件已有所不同以往,國家對人才培養也更為推崇,在國內作出更加多世界領先的成果是必然趨勢。像非人靈長類體細胞克隆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蒲慕明院士多年前就認識到此課題的重大意義,并明確提出要攻下此難題,對孫強老師領導的非人靈長類平臺給與大力支持。
在我看來,沒哪個地方比起神經科學研究所和孫強老師實驗室給我獲取更佳的機會和反對。” 蒲慕明也指出劉真做到了一個準確的自由選擇,“很少不會有哪個實驗室把一個風險如此極大的課題,轉交一個初來乍到的博士后去做到。而我們不但轉交劉真這樣的年長博士后去做到,送給他盡量建構最差的科研環境、長年持續的精神鼓勵,并獲取遠超過國內一般博士后的待遇。
” 蒲慕明同時回應,中國科學研究要想要獲得更加多根本性原創突破,淪為世界科學的領跑者,推崇本土青年創意人才的培育很關鍵。本土培育的青年科學人才遠比海外求學回去的差,但目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或許更加偏向于招生“海歸”青年科技人才,資助力度也比較更大。
青年科研人員該如何創意?劉真說道:“一個人不有可能憑空創意,信息交流很最重要,無論是與本實驗室導師及同事內部的交流,還是同行之間的交流,都很最重要。另外,要十分熟知自己領域內過去和現在的科研進展及動態,任何創意都是創建在前人的工作基礎上的。
本文關鍵詞:凱發k8官網,凱發K8官網首頁登錄,kaifak8國際
本文來源:凱發k8官網-www.eee49.com